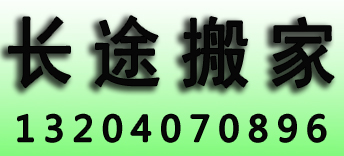河西走廊面临着的世界性难题:土地沙化和荒漠化的问题日趋严重;沙尘源的增多为沙尘暴推波助澜,任何的环境变化,都会造成沙尘天气;越来越多的沙尘天气,致使生活在风沙一线的乡民们艰难前行。
年3月9日,记者曾到瓜州县环城乡下干沟村采访。当时风沙刚停,下午4时,苍白的太阳如剪纸般贴在灰暗的天空中,尚未退去的沙尘,弥漫在这个村庄里,疏勒河河床上流淌的不再是清凌凌的河水,被风梳理成羽状的沙丘对村庄形成包围之势。65岁的倪老汉一遍遍感叹:“风沙把人害死了……”
时间仿佛已经停止,眼前的一切似乎永远被定格在昨天:村庄还是那个村庄,虽然没有刮风,但村庄四周都被沙尘紧紧包围,土苍苍的村街,在炙热的阳光下反射着灰黄的光。背靠干涸的疏勒河,两排破旧的土坯平房、10来户人家和10多名留守村民,尽显村庄的败落。70多岁的倪老汉病重在医院治疗,在他家衰败的房屋里,许多赶来的村民感叹:“不要说已经10年,就是再过10年,你来也没什么变化。要说变化,或许就是被沙埋了。”
都是沙尘惹的祸。”组长李俊林直言。沙尘暴,在村民的心里蒙上了厚厚的阴影。
68岁的党志才一个劲地叹气。老人在村里生活了一辈子,用村民们的话说是“沙里生、沙里长、沙里埋的人”,对沙尘的危害深有体会。老人告诉记者,早在上世纪60年代前,疏勒河水流不断,这里水草丰美,可谓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。那时候,村庄前后都是水,村庄处在一块干梁上,村民们担心河水淹没了村庄,希望这里永远是一道“干涸的沟”,所以把村庄起名为“干沟”。可到了60年代以后,距这里30多公里的双塔水库截住了河水,疏勒河断流,地下水下降,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干沟”。水草丰美的景色逐渐没有了,随之而来的是肆虐的风沙。
据李俊林介绍,村里原来有30户人家107口人,风沙逼着村民往外迁,现在老住户仅剩9户,其余几户人是外来的移民。即便如此,村里的常住人口也只是些老人。学生娃娃在县城上学,家长跟着儿女陪读打工,日子久了扎根县城,“租房生活也比这里强”。只有在春种秋收时,村里才能看见“人”。
村东800米处,一道南北走向的“沙梁”是石岗墩防风治沙保护区最东的边界线。
李俊林说,这道“沙梁”其实是水渠,被沙石填埋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若不是近前从村民挖开的一处豁口细看,根本看不到水渠的痕迹。村民在淤沙中挖开的一道小沟槽中,旁边一眼机井中抽出的一股细流缓慢地流向附近的农田。眼看着贵如油的涓涓细流渗入沙海,村民们心痛不已。
李俊林告诉记者,过去,全村480多亩耕地都靠这条水渠引水灌溉,渠道畅通时,6天6夜就可以完成全村灌溉。而现在,渠道被沙填埋,有限的人力已没有能力挖沙挑渠,村民只得放弃通过水渠引河水灌溉的想法,改用机井,灌溉一轮水少说也得40多天。
沙进人退,耕地被风沙一片片吞噬了。这几年,村里已有20多亩耕地被沙土彻底废了。
4月4日,酒泉金塔县鼎新镇夹墩湾村,巴丹吉林沙漠边缘。
枯黄的防护林树丛,斜斜地站立在漫过树腰的沙丘中,看上去,似乎不久即有被黄沙压倒或吞噬的危险。黄沙边的是数块等待耕种的农田。
9年前,因为无法忍受“十年九旱”的贫困生活,杨积业举家从青海来到金塔这个叫夹墩湾的地方;9年里,饱受风沙之苦的杨积业,又想回老家,呼吸“没有风沙的空气”。
这一切,和一条渠有关。
黑河经这里由南向北流向内蒙古,村庄的西面,是巴丹吉林沙漠连绵起伏的沙丘。夹在水与沙之间的这个村庄叫夹墩湾。杨积业说,沿着沙丘前行1000多米,有一个叫沙槽子的地方,那里有他的4亩农田。
浇水困难呀!”杨积业摇着头连连感叹。修好的水渠只能用一年,等到春天,一场风沙过后,2米多深的渠道就不见踪影了。“只好再修。沙少的地方,清了沙就能用。但沙多的地方,只能往前移。每年2米多,9年来,我修了9条渠。”
一年前移2米多,9年少说也是18米了。“不止这个数。”杨积业说,“大沙包不知前移了多少,有很多树木和桦秧子都被沙埋了。照这样下去,即使我不走,也没法生活了。”
在他家的炕沿上,杨积业的3个孩子正在写作业。大女儿已经上高二了。她说:“风沙太大了,有时刮得学都上不成。吃完饭,碗底就是一层沙子。”她似乎对父亲未来的去留没有多的想法,“再有一年就高考了,只想好好学习,考上大学,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。”
赶紧考上学走吧。”70岁的李生军感叹说,“水渠年年移,沙窝子边上好多胡杨林都旱死了。”
在夹墩湾长大、住在沙窝子边的李生军记得最清楚的是:“每年春天一刮风,天上全是沙,风停后,院子里的沙有几厘米厚。”
站在院落边,望着近在咫尺的沙丘,白发苍苍的李生军感慨不已。“以前不是这个样子。”现今被沙丘占据的地方,原本生长着许多林木和草丛。林木一旁的洼地里,积滞着很多灌溉之后剩下来的“闲水”,因为有这些水,很少发生林木枯死的情况。每到春暖花开,村庄外的林地里到处是吐翠露绿的林草。后来,村外洼地里的“闲水”越来越少,林木旱死得也越来越多,再后来,连植树都开始缺水了。
枯死的林木越来越多。“每次一刮黑风,黄沙就朝村子的方向来了。”每年春天的沙尘暴,让看着沙窝子步步向前的李生军心里生疼。
凶猛的沙丘径直扑向了它面前的这个相对柔弱的小村庄。
“家园像扛在肩上的包袱。”已经搬了4次家的贺兴田老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。
比李生军小一岁的贺兴田见证了沙漠朝着自己家园前进的足迹。
贺兴田第一次搬家时只有9岁。那一次,眼看沙丘逼近房屋,父亲带着一家6口人,在村里选择了一处地方,重新建房落脚。比起旧宅来,离沙漠相对算较远了,但只过了短短几年,好不容易安上新家的贺家人心里的暖意还未消散,新房就又处在沙丘的脚步前了,他们不得不再次搬迁。贺兴田说,第一次搬家后,他们只“安稳地”度过了8年。
16岁,第二次搬家。父母年迈,家里没有壮劳力,经济条件也不行,雇不起别人来帮忙,年幼的贺兴田挑起了建新房的担子。尚未成人的贺兴田,一天要打200多个建房用的砖形土坯。
1960年,贺兴田第三次搬家。“之前,老父亲过世了。”贺兴田说,虽然没有背井离乡,还是在老宅附近的地方重建,但每一次搬家,一家人的心里都不好受。
沙丘还在前进。1975年,贺兴田又搬了一次家。贺兴田说:“我被风沙赶了一辈子。”
贺兴田搬了四次家,始终没有离开夹墩湾,而他所在的夹墩湾3组的村民中,很多人选择了离开。
1996年,夹墩湾共有14户60多口人,而现有的12户人中,土生土长的夹墩湾人只剩下3户。“经济条件稍好点的,哪里能落脚,就到哪去了。”夹墩湾村支书白展雄说,搬走的村民流向四面八方,有的就近到金塔县别的乡镇落户了,有的则投亲靠友,远赴异地。
尽管万般不舍,但贺兴田和邻居们不得不直面现实:沙漠越来越近,耕地越来越少。据白展雄介绍,上世纪50年代,夹墩湾三组有300多亩水浇地,现在12户人的全部水浇地只有170多亩。
今年初春,沙漠边上的夹墩湾村民再次饱受沙尘暴和浮尘天气的袭扰。“沙丘就在我们的地边上,随时都有可能吞掉农田。”一名村民说,“看来,我们有可能面临第五次搬迁。”
去与留,村民在犹豫徘徊。
正新村处在腾格里沙漠风沙线的最前沿,以前每户村民有3亩耕地,种植棉花、小麦等作物。这些年因为缺水多风沙,许多人被迫举家外迁。从上世纪80年代起,全村有近300人迁移。”民勤县正新村五组组长陈友来说。
当过民办教师的陈富国今年72岁,家住民勤县红沙梁乡新沟四社。2008年,儿女在村东头给陈富国老两口盖了3间新房,因为他们原来的5间老房子被风沙摧毁了。
陈富国说:“村里的房子逐渐被沙子摧毁了,一些人无法忍受,迁往新疆、内蒙古、四川、东北等地了。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,200多人口的村庄,人口减少了近一半。”
与红沙梁乡新沟四社相比,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民勤县东湖镇下润村六社的状况似乎要好一些,然而,风沙还是逼走了不少人。
据下润村支书沈嘉道介绍,现在这里的村民种植养殖的收入加上退耕还林的补偿,人均年收入达4000元。现在尝试着在沙丘下种苁蓉药材,指望着卖个好价钱,可是,饱受沙患的村子里,年轻人和有门路的人还是陆续离开。“原先200多口人,现在在册人数只有124人。留守的人中,壮劳力不足15人,小孩不足10人。”
沈嘉道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工作,儿女们让老两口到他们那里享福。他说:“故土难离,我们不想离开这里啊!”
沙进人退,除了村民为寻求生存空间而自行迁移外,还有政府不得已组织的整体迁移。
西渠乡煌辉村四组村民盛汤国、盛禹国算是该村最后的守望者。
2007年,盛禹国随着村组的整体搬迁迁入蔡旗乡。2008年12月,独守煌辉村的盛汤国也离开故土,搬迁至蔡旗乡。至此,在西渠乡煌辉村剩余的140余户村民全部迁到了蔡旗乡蔡旗农场,这是煌辉村最大的一次搬迁。
煌辉村距蔡旗农场180多公里,位于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——红崖山水库的不远处,水量较其他地区充足,这一优越的条件对于农民来说最有诱惑力了,然而,为了生态,生活不得不改变。
整村搬迁是政府的安排,为了生态,没理由拒绝。”盛禹国说。
风沙,影响甚至侵蚀着年轻人的思想。1988年夏天,当时在民勤三中读高中的白生钢因为家庭收入不好被迫放弃学业,成家后,他将希望寄托在了一双儿女身上。
一定要考上大学,离开这里。”白生钢的女儿白丽是民勤一中高二年级的学生,受父亲的影响,白丽暗自下决心要离开。白丽的弟弟虽然才上小学三年级,口气更为坚定:“以后,就是打工也要离开这儿。”
面对酷烈的生态环境,村民做出怎样的选择都无可厚非。而无法回避的现实是:面对沙尘,如何改变才是我们正确而科学的选择?
文 本报记者 阎世德 鲁明 董开炜